13-10-2010【匈奴未灭/黄进发专栏】徐威雄的文章《也谈“华教的敌人”--回应黄进发》对拙作《迦玛是华教的敌人吗?》基本上做出两个批评。
第一,徐氏认为,拙作指出“迦玛对华教界之所以深具震撼性,是因为:一他以流利的华语来反华教;二是他举中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华人国家’为实例来反华教。……这两个高明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手法,让华教人士有如‘吃了暗亏’,以致于‘投鼠忌器’不知要如何批评他,所以只好情绪化地叫他闭嘴。”,而其实“这两个论点完全是‘伪命题’,是作者自己想当然耳的臆测,并不合实际状况。”(双引号内为徐氏原文,这精简版的解读与我原文脉络稍有出入,虽然这不妨碍基本讨论,但有兴趣者应该同时参考拙作方作论断。)
第二,徐氏‘赞成’我指出华教真正的敌人是‘民族国家’,但却认为我的质问:‘爱华教,有力地为多语言教育系统的存在辩护,就要从根本上批判民族国家的概念;今天骂得很凶的人准备这么做吗?’“不尽符事实”。
徐氏认为:“如果这里指的是所有的华教人(而不只是今天在骂迦玛的那几个人),那这句话完全错了。华教论述里真的没有批判“民族国家” 吗(深浅则是另一个问题)?试看董总在评论《五年教育蓝图》的总意见书里,就对官方欲通过单元教育来建构民族国家的做法予以严律批判。”,批评我没有“读读五十年来华教的历史文献”。 (双引号内为徐氏原文)
我对第二个问题深感兴趣,觉得此事关系华教对迦玛类似批评者的回应,因此先予回应。
华教如何批判民族国家?
拙作没有一竹竿打翻全船人、指责华教人士都没有批判民族国家的意思,徐氏自己也看得明白;不过,如果徐氏认为五十年来华教的历史文献对民族国家有深入有效的批判,我诚恳希望徐氏能开出一张具体的书单让我们学习。
非常明显的,华教不是从来没有批判民族国家——董教总才刚刚和教育部划清界限,表明反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言”的民族国家概念;而是华教批判的往往只是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的终极主张是一个民族应该只有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也应该只有一个民族。易言之,社会文化的集体(民族)必须与地缘政治的集体(国家)结合,不容分割。民族国家在文化上的霸权高压,正是出于政治上保持统一的需要。
当“董教总”在批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言”四位一体的思想时,它本身的理想是什么呢?“一个国家,多个民族”?而每一个民族之间是不是“一种文化,一种语言”?
具体地说,华人是不是都要说华语/以华语为母语的义务?还是说,华人要说华语/以华语为母语时,其权利不可受到压制?语言作为“义务”和作为“权利”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民族国家把所谓官方语言强加于公民/居民身上,不正是出于“义务”的概念?沈慕羽精神奖其中之一刚刚颁给一位确保其服务学校的华裔生必须选修选考中文的老师,如果其学生举起权利/自由的大旗反对,我们能不能接受?
简单地说,民族国家对文化的选择是官方认定的——你既然住在这片国土上,你就要服从国家的安排。民族对文化的选择也是群体认定的——你既然生在我们当中,你就应该和大家保持同样的文化、语言、宗教。
许多华人对马来人必须是回教徒的国策感到同情;转过头来,如果华人就必须说华语,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被同情?
迦玛轻佻的语言后面,正是以马来西亚“民族国家”之矛,攻马来西亚华裔“民族”之盾。
现有华教论述反对“单科主义”的依据是华教不止是语言教育,而是文化教育和民族教育。超越语言的文化教育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民族教育呢?是要养成“中华民族”吗?
那么,每年1万名华小非华裔新生是不是准备被同化成华人呢?推论下去,如果不准备接受同化的非华裔生,华校都不能够招收,那么,华校就只能是纯华人学校?对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本来就是华校的目的,因为到最后,华文教育应该是华人的华文教育,而不是华文教育而已。问题是,我们就无法避免“族群隔离”的指责了。“族群隔离”一定错吗?当然不,如果你要维护一个边界明确的民族。
简单地说,“民族教育”论述的罩门是:它所要构建的“马来西亚华裔民族”是不是准备堂堂皇皇站出来和系出同门的“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对抗?
迦玛有没有暴露华人的双重标准?
我基本的看法是迦玛对华教的批评暴露了部分华人的双重标准,因为他用华语批评,并且举中新两个“华人国家”为例,让一些华人投鼠忌器。必须强调,我并没有说,这是迦玛被批评的全部理由,否则,在同篇文章中批评迦玛的我不就是自括耳光?
徐氏批评说:“华教人士之维护华教,自有其历史渊源、民族情感、正当权益、学理依据等等,但从来没有过以中国或新加坡为援据为理由的,也从不会因为中新两国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而患得患失。”这段话很巧妙,前半段从“历史渊源”到“没有过以中国或新加坡为援据为理由”,我都同意,但是,这能证明一些维护华教者没有双重标准吗?后半段“不会因为中新两国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而患得患失”正是我们所要检验的命题,徐氏怎能就把命题直接当作结论呢?正确的检验标准是,我们有没有用自己对母语教育的要求来审视、检验中新两国的教育制度?
中国和新加坡虽然都是所谓“华人国家”,其拥护者却不大相同。就新加坡的部分,我清楚指出会回避新加坡单一源流政策的是“崇洋的华人”(原文第十一段),徐氏用陆庭谕老师对新加坡的批评来回答我,岂非把陆老当作崇洋华人?用这样张冠李戴的论据来指责我提出“伪命题”、“想当然耳”、“臆测”,不管是不是疏忽误读,都对我不公平,也对陆老不公平。
就中国的部分,徐氏指出中国数个省份其实有彝族语言学校,与迦玛所引的漾濞彝族自治縣例子不符,我感谢他用心指出,让我们的讨论有更准确的脉络。我查过该县教育局的官方网站,里面没有不同源流数据,即使政策上也只是强调“在不通晓汉语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小学,可以用少数民族语言辅助教学”(第四十条),显然迦玛所得资讯没有错误,最多只是以偏概全。
我印象中迦玛曾经不止一次引中国的经验说明单一源流教育系统的合理性,后来只找到《中国彝族母语》一篇文章。以“国情不同”为中国语言教育政策辩护者,或者哑忍不反驳迦玛者,我知道绝对不会只有黄玉凤一人,徐氏当然可以质疑这样的人在华教建制里是不是很多,我就不辩护,留给读者自己判断了。
黄进发是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比较民主化博士候选人,现任私立大学讲师、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主席。
http://ww.merdekareview.com/news/n/15227.html
2011年5月31日星期二
订阅:
博文评论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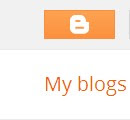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