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廟對我來說是個深不可測的地方。大概以前看過許多深山古剎的老電影,那種隱蔽在山中的荒涼廟宇似乎都蘊含著感人的故事,那晨霧,雨珠,煙氣,殘竹都像是很早就存在那里了,它們深邃地靜默著,等待結緣者的降臨。這種老廟里造就了小倩和寧采臣的悱惻戀情,也曾埋藏腥風血雨的江湖故事。
和電影里的深山古剎相比,我們這里的神廟當然不是荒涼的。多數的時候,神廟里人聲沸騰,充滿著節慶的氣氛。為膜拜,為祈福,或是禱盼願望的實現。
其實小小的廟宇承載著普通老百姓的信仰,一切交付予神明,就不是本身需獨自承擔的孤單責任了。在神明的庇佑下,一切都有了穩定的寄托,就有了「共鳴」的紐帶。
孩童們對神廟都很好奇,也當成一個神秘好玩的地方。那些高大昂然的神像不說話,卻無時無刻不在接受眾人的敬仰。孩童們被告知「不能亂說話!」,這對他們是新鮮的;而挑戰權威,一直都是孩童熱衷的遊戲。
各種各樣的拜祀用品羅列,廟里的信眾唸唸有詞,構成一幅奇異的景象。孩童們在疑惑,究竟這些木然不動的身影里頭,真有「靈」嗎?大人們沒法回答這些問題,就拿出那句老話來敷衍:等你長大自然會知道。
與孩童比起來,年輕人就成為冷漠的存在了。他們多數受到現代教育的熏陶,不信鬼神,就算半信半疑,也被教導必須「敬鬼神而遠之」。這大抵是東方文化「明哲保身」的根髓吧,在行動上循規蹈矩。光明磊落地待人處世當然好,卻又似乎少了一些靈魂的激盪了。
迷中有信,信中有迷?
「迷信」二字如此深烙腦門,成為一個輕易評價人類行為的詞彙。如果年輕人也喜隨家中長輩到廟里對神明頂禮膜拜,或許要被說成「迷信」之流了。究竟是「迷」或是「信」,或者迷中本有信,信中自有迷?斷不是三言兩語或單層面思維可推斷的了。
我喜歡到神廟去,也不完全因為宗教因素。神廟和佛堂是不同的,前者大抵為儒、釋、道三者交融的本土教派,屬民間宗教的一種;而佛堂則屬大乘佛教。佛堂宏深壯闊,氣勢滔滔;而神廟則大小不一,個別供奉天下諸神,各有名堂,多為當地信眾出資所建。佛堂里的佛像靜穆慈悲,而神廟里的尊座卻無奇不有,各府王爺元帥和玄天上帝並立,令人眼花繚亂。
在心思煩亂的時候,我喜歡到佛堂里靜坐;而平常時候,我更喜歡到神廟探秘。廟里的神祇有親和力和不怒自威的莊嚴相,許多神話故事充滿人性的光輝。分佈於我國各地的廟宇,其實是非常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是一門深具學術價值、值得深入探討的學問。
雖然在「迷信」大網的籠罩下,它們仍存在於亞州各國的亞裔社區,一直是香火鼎盛,信眾不減。這也就說明了其存在的客觀價值。西方人流行看心理醫生,有人說,東方人的心理醫生就是廟里的神靈,此說似不無道理。
研究東南亞宗教的學者指出,馬來西亞本土華人神廟有著以下的功能:其一,當作本地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想當年我們祖先南來蠻荒,神廟存在的意義就如「會館」,卻沒有「會館」的地緣性質,神廟以宗教來促進團結,加強交流,是完整社會結構的重要存在。
再者,神廟存在本地,亦是本地華人展示其經濟力量的憑證,對本地華人身份認同的確立有著一定的影響。社會現象一直是人們心理變遷的展示,宗教學作為社會學與人類學的一環,成為探討人類思想發展史的有力工具。
鄙薄他人即鄙薄自己
楊牧的《疑神》里記錄一段有趣的話:
「宗教的首要是教人謙遜。一個人若是為有了宗教信仰而驕傲,自滿,甚至因此鄙薄無信仰者,或動輒排斥與他信仰稍稍不同的人,便表示他自己還沒有找到信仰,所以,他自己也在他自己鄙薄和排斥之列。
一個人若因為自覺接受了上帝,心里喜悅,但又猶豫,感到有點難為情(這其中自以知識分子為最顯著),便時時於言談筆下帶有defensive的防禦意味,以及offensive的攻擊企圖,也表示他去宗教所願教他的謙遜甚遠,他再怎麼說都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
這句話有趣之處就在於,它指出了宗教與個人的對立,太看重自我(ego)的人較難寬容地接受宇宙間的某些超驗的意識,因為這類人特別喜歡質疑一切。偏偏「捨我」就是大部分東方信仰所要求的形態。
在不同時空下,神靈的的故事各異,唯一把它們接連在一起的,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與冥想。就好像我們都渴望快樂,拒絕痛苦,珍惜成功,害怕失敗,一切是相悖的,其實又是相通的。就像一個圓,開始與結束都是同一個點。這大概也就是每個人心靈渴望的圓滿吧。而在神廟里,我看到各種心靈的火花碰撞,並留下了激盪之後殘餘的沉著。
http://www2.orientaldaily.com.my/fread/2arC0ct21Hh01UrQ0u7B832F2gGS8Avb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Theanlyn Blo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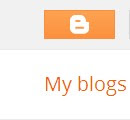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